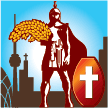作者:黃雪卿 轉載自「國際短宣使團 - 電子資源中心」(IFSTM eResource Center - https://eresource.ifstms.org/) 反猶主義早在第一世紀基督教教父時期已經存在,有一些教父倡導主耶穌之死,猶太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當猶太人分佈歐洲各地,都感到反猶主義的氛圍,他們經過幾個世紀的種族排擠和歧視,形成兩個階層的猶太人。一批是聰明有學識之士,是當時貴族的代理人,屬於上流社會的富人;另一批人,因著固有的信仰規條,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,活在自我封閉的社區。 到18世紀末,在德國柏林發起「哈斯卡拉」(Haskalah השׂכּלה) 的啟蒙運動,發起者主要是一班猶太商人與及有學識的猶太人,他們目的是讓當時生活在定居點/貧民窟(Ghetto)的猶太人,開擴他們對社會的視野,增加他們學識,可以將他們帶入歐洲主流文化裡,這意味著在學校課程中增加世俗科目、採用當地語言代替意第緒語 (Yiddish)、放棄只有黑白色的傳統服裝、改革猶太教一直以來固有的傳統和規條、從事新興的職業,以增加他們就業機會。後來運動傳播至東歐。詳情可以瀏覽以下網站: 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topic/Haskala 但「哈斯卡拉」的啟蒙運動,並不能改善人們對猶太人的歧視,及至19世紀後期,新一輪反猶浪潮,導致錫安運動的出現,錫安運動實質是民族復國主義運動。以下是由錫安主義到以色列立國的過程: 在18世紀已有拉比們倡導猶太人要回歸以色列,重建家園,拉比們重點是在聖經的教導,遵照神的應許,旨在復興猶太教,沒有政治意味,但當反猶氛圍高漲時,就會加強這方面的教導。 在18世紀末,德國柏林發起「哈斯卡拉」(Haskalah השׂכּלה) 的啟蒙運動。 俄國的猶太人醫生利奧平斯克 (Leon Pinsker—1821-1891年) 是錫安主義先軀,他早期認為:如果猶太人獲得平等的權利,問題就能得到解決,認同「哈斯卡拉」啟蒙運動可以解決猶太人根本問題,但是反猶主義一直高漲,直到1881年,他推翻自己的信念,成立錫安主義者機構—錫安愛國者 (Hibbat Zion—Lovers of Zion),1884年在德國城市卡托維茲 (Katowice,現今在波蘭境內)
【日本樂散步】花嫁
作者:Chion 「花」常用來比喻女性的一生:初生胚芽萌發,在陽光雨露均霑下漸長,含苞待放、花蕾滿枝至淍謝枯萎。淡白粉紅的春天一過,日本迎來七彩繽粉的初夏,也是盛產花嫁的季節。日文的「新娘」,漢字寫成「花嫁」,意思是一生最盛開、最姹紫嫣紅之時,如花似玉的少女要嫁人了。還有一種說法,花也等同「新」的意思,夫家尊重新嫁入的華麗新婦,用鮮花佈滿花道迎親入府,因而稱新娘為花嫁,而新郎就是「花婿」,花朵的女婿,很浪漫、很應景的漢字。 西洋文化普及後,女孩們憧憬穿著白色婚紗,走過鮮花滿地的走廊迎向所愛的人,因而日本有很多只為舉行婚禮的教堂。和婚紗一樣,出嫁時女子的日式婚服「白無垢」是完全純白的和服,由內衣至外服及頭飾都是白色。遠古的室町時代開始,白色代表太陽之色,是神聖的顏色。白色也表明身心純潔無瑕的新娘,決心把自我捨去嫁入新家,「從今以後只染上丈夫的顏色」,全心全意與夫家合一。白色的布附吉祥的精緻花柄圖案,如鶴有長壽和婚姻和諧的象徵,鳳凰喻意長生不老,牡丹代表繁榮,櫻花則是新起點等。新娘梳起的正裝頭髮,會被白色娟布卷成如帽子般的「角隱」遮蓋,表明新娘會把怒氣、忌妒等惡「角」收起順服丈夫,免自己變成有角的鬼怪,是昔時民間的小迷信。最後戴上白綿帽子如頭紗,婚禮完結之前它把新娘的頭及臉都半遮蓋,不讓外人見到容顏表示忠誠於丈夫一人。 「白無垢」配有3件小物件,花嫁手拿著「末廣」 — 小扇子,象徵幸福蔓延擴散;裝飾在胸前的「筥迫 」— 化妝包,裝著鏡子、和紙巾及替換髮飾 ;及「懷劍」—防身小刀,象徵武士的媳婦在危險中能自我保護,也能如男子般自豪地切腹死去,有著男女平等的氣勢,也有著守護的意思。「白無垢」穿著複雜及行動不方便,近年的新人多穿來拍攝婚照,或舉行傳統的神社婚禮時才會穿著,普通的婚宴都偏愛鮮艷火紅的「色打掛」—有色豪華和服。 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思想,昔時上流家庭的孩子們都是家族的財產,女兒從小就開始「花嫁修業」,培訓出處理家事精明、有修養懂禮儀的賢妻良母,代表家族體面出嫁。19世紀初,女孩開始能上學受教育, 生於愛媛縣的婆婆說:「我家很貧窮,上學也要背著幼弟,日常家務就跟著祖母、母親身邊學。女兒上學校時,除了學語文算計外,也著重花嫁修業,學校也教女兒經營家庭的正規技能及修養,如煮飯、洗衣服、日式及西洋裁剪、打掃等,還有茶道、花道、書法、舞蹈、穿著、禮節及樂器,克服不愛吃的食物也是修行之一。那年代什麼都要自己做,女兒的嫁妝就添了縫紉機,為幫助她婚後生活輕鬆些。」 當人問剛入藉的新婦鈴芽,到底花嫁修業還有必要嗎? 她婚後的結論是「不是必須的,但是學了絕對沒有損失」,她認為有所準備才能更有把握地應付自如,讓自己及未來的家人都過得好。 忙於為事業打拼的鈴芽,她的日常生活一直由全職主婦的媽媽照顧,為了以後雙職小家庭能有餐好吃,就到料理教室上了個花嫁基本調理班。除了蒸煮煎炸、切法及調味,還有教授蔬菜配搭、營養管理、時短速成料理、選購和保存食物等,真是讓她大開眼界。搬到新居,疲乏的兩人被下班後還要做大堆沒有完的打掃、整理等家務弄得累上加累。媽媽看不下去,在休息日就著手一一地教,由洗碗、洗衣服至收拾、家計薄等,還有如何讓老公愉快地分擔家務。鈴芽摟著媽媽,感到母親太能幹了,安頓好一個家背後有這麼多學問,她這個新婦還有很多東西要學。 蒙恩得救愛主的信徒也像花嫁般,啟示錄19:7-8中,異象中使徒約翰看到「因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,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,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。」就如花嫁裝飾整齊等候丈夫主耶穌,在祂再臨時親迎娶自己的新娘。心越重視男方,花嫁也越專注,務求能以最美麗、最取悅花婿的姿態出嫁;愛主的人也一樣,期待當中的喜樂,便會越盡心盡意為所愛的,努力學習聖經,靠著聖靈操練品行及結出美好的果子。 花嫁修行的真正意義,不止為了配偶,也為了新婦能愉快、快速適應全新的生活,成長、磨練成為超棒的媳婦兒。 「入藉」小常識:日本是戶口制,結婚時要由原生家庭轉戶藉到丈夫家庭,稱為入藉,入藉一詞現在也等同宣告結婚了。
【雪說以色列】之八:基布茲Kibbutz
作者:黃雪卿 轉載自「國際短宣使團 - 電子資源中心」(IFSTM eResource Center - https://eresource.ifstms.org/) 驟看「基布茲」這個詞,真不知道這是什麽東西?台灣翻譯為「集體農場」或「集產農場」,而中國把它翻譯為「人民公社」,正是將它的意思翻出來了,「基布茲」所有成員,是以共產思想來生活,沒有私人財產。 位於以色列加利利湖南端的 Degania 基布茲,被譽為「基布茲之母」,那是以色列的第一個基布茲,在1910年第二次移民潮下,由十男二女建立。今天,基布茲的總數約270個,他們實行共產制,在基布茲內是凡物公用,成員的收入全部由基布茲統一派發,沒有私有財產,那是一個名符其實的「各盡所能,按需分配」的生活模式。他們經營的不只是農場,凡是可以賺錢的項目,例如酒店、工廠、博物館、餐廳等,他們都會發展,他們所謂的共產,只限於基布茲的成員,在以色列政府是屬於非營利組織,他們可以向政府申請義工簽證,協助基布茲的運作。 基布茲在鄂圖曼時代已見雛型,當時從俄羅斯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,深受共產主義影響,於是透過基布茲來實踐。他們相信人人都是平等的,所以不管是醫生或教授等專業人士,都要勞動耕種,並收取相同的工資。他們也可以自由地在基布茲以外工作,條件是要獲大多數成員通過,並且要把工資上繳,收取基布茲發與大家一樣的工資。至於在教養孩童方面,孩童平時是生活在一起,集體接受教育,在安息日才回家與父母共聚天倫,其中的好處,是孩童不會因為父母供應他們物質而互相比較。但現在已經有所改變,孩童都可以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庭住宿。 有一次,帶團參觀Ein Shemer基布茲,導賞員說他們在初期連婚禮場地、婚紗和婚宴菜肴都一式一樣,後來經過改革,現在已有比較個人化的安排了。另一次,我與朋友到北部Blum基布茲渡假,朋友說那基布茲是製造女士剃毛刀刨起家的,後來發展不俗,產品更分銷到世界各地,特別是美國,不久基布茲更發展酒店業。難怪有人說,女性的金錢是最容易賺取的!在革尼撒勒(Ginosa)平原有一個基布茲,除耕種和養牛外,更有旅館和碼頭;那裡有兩個博物館,分別放置耶穌時代的漁船和介紹當地的開墾歷史。 這樣的基布茲,培育出不同的意式形態的猶太人,以比喻簡單說明之,有一名農夫在種地,他認為自己在履行應有的責任;另一名農夫認為,為了讓整個基布茲有農作物吃和賺錢,所以他時常思想和嘗試,如何可以多種多收;第三名農夫卻說,雖是農夫,但我是在建立一個國家,讓國家有糧可食。後來,第一個農夫仍然是農夫,第二個成為農業專家,第三個則成為國家領袖。確實,很多立國初期的領袖,都是基布茲出身的。 基布茲是立國前的產物,他們不計較自己的利益,為了國家作出供獻,但到20世紀初,國家穩定下來,人民的意識形態也有改變,開始為自己籌算,後來演變成類似合作社的合作農村
【雪說以色列】之七:回歸潮 (Aliyah)
作者:黃雪卿 轉載自「國際短宣使團 - 電子資源中心」(IFSTM eResource Center - https://eresource.ifstms.org/) 希伯來字Aliyah,意思是「上行」的意思,猶太成年男子一年有三次會上耶路撒冷過節,稱為「上行」,而詩篇120-134,總共15篇,也稱為「上行之詩」,因為在過節時,往耶路撒冷的路上,或登上聖殿階梯時,[1] 都會誦讀這些詩篇,今天卻指猶太人回歸以色列,稱為Aliyah,用現代術語即是「移民」。先知以賽亞,耶利米,以西結早早已經預言神會將流散的猶太人從地的四方,再次聚集到以色列。所以,重建自己家園的渴望,一直深深植根於猶太人的心中。 主前586年,南國滅亡後,猶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,但仍然有猶太人居住在以色列這塊土地上,上一期「聖殿被毀後,猶太人何去何從?」已經提過,現在不再多講。直至十九世紀後期,反猶主義一直高漲,這時錫安主義的出現,[2] 更加堅定他們回歸的決心,所以才有一批一批的猶太人,回到當時被鄂圖曼統治的「巴勒斯坦」的地方,但猶太人仍稱這地為「以色列」。 第一波(1882-1903)— 俄國沙王亞歷山大二世遭暗殺後,在1881-1884年間開始大規模反猶暴動,引發第一波回歸潮發生。這個時候,移民大多數過著集體的農業開墾生活,當時為了開墾土地,面對蚊蟲滋生,死的人不少、還有鄂圖曼時期的重稅、阿拉伯人的敵對勢力,生活相當困難。在這幾年之間約有27,500名猶太人回歸。 早在第一波回歸潮之前,在1870年查爾斯·內特(Charles